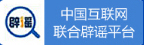8月13日,小说家、艺术与文学评论家吴亮携他第二部长篇小说《不存在的信札》,亮相上海书展。70后女作家走走与他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文学对谈。
对谈中,吴亮提到,自己写《不存在的信札》时,想到了童年时的天井,天井外的景色总是时常变幻,尽管始终处于同一个世界,同一个环境。这也成了吴亮写《不存在的信札》的语言背景。这部长篇小说,吴亮从虚构的书信入手,展开一场由女子曼达揭开的上海滩艺术圈流动的盛宴。失踪的情感、无法回应的安慰……似有若无的记忆。一面影响着每一个身处回忆深处的人,一面塑造着特殊时代一个个不同的人与他们跌宕又充满犹豫的日常。
吴亮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,他以罕见的敏锐直觉,建立着自己的文学与艺术审美。成为一代人心中的文化符合。近年来,他投入小说写作,以独特的语言地貌,建立着自己的文学秩序与艺术野心。

《不存在的信札》以诗意的叙述,沉浸式的话语,重现上世纪九十年代,美术圈和文学圈里的生活片段,看似浮光掠影,却是内心深处的真切交通,兼及宗教、哲学等等的思考。没有署名的信,面目不明的写信者,围绕一个名叫曼达的神秘女人,彼此缠绕又模糊不清的关系……吴亮以不可思议的如谜一般的写作姿态,构筑了一座真实的碎片大厦,却在大厦完成时揭出一个谜底——也许这一切根本就不存在。
著名评论家程德培表示:我们在《朝霞》中已经领教过吴亮式的断片,不过,那时的断片只是全书的一部分,了不起是半壁江山。《不存在的信札》不同了,全书都由断片组成,加上叙事者的隐身且不断轮替,增加了阅读的迷惘。那些温文尔雅秩序井然的叙述全然不见踪影,人物沦为言语的图像,是一种讲话方式,混乱的讲述、段落的剪辑无序、字里行间布满了藏头文字、谜语和暗示,言语断断续续,不经意的一瞥,稍纵即逝的瞬间,一种隐秘而敲打人心的倾诉、交谈热身,我们必须用心琢磨他的语意,努力去添补沉默的故事才行。用莎士比亚的话说就是,一个人长眼睛,最大的用处却是去赶这条黑暗的路程。
而在如今这个复杂的时代,吴亮《不存在的信札》既没有宣传文案,也没有作者简介,甚至整个封面没有一句话涉及文本复杂暧昧的意旨,这本身就是一次特立独行的文学革命。那个八十年代写过许多先锋作家文学评论的理论家,居然如今正在成为那代人最具文体意识和艺术野心的小说家之一,这让人神奇,又让人对吴亮今后的作品无限期待。朱虹